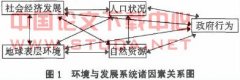一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更恰当地说是从新中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迅速一统天下,给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带来巨大的影响。之前存在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被一起仍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者成了民间的隐匿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推动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对中国每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数不胜数。但是我没有要去历数这些成果的意思,本文要谈到葛兆光先生的巨著《中国思想史》,所以就不得不从学术的一统化说起。
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统天下,学术界当然是莫能例外。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就放弃了以前的进化论,转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指导思想,其主要意旨是: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也是有着某种目的和方向,在历史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发展,后一个时代必然优于前一个时代。照此类推,后一个时代的思想也必然优于前一代的思想。于是学者们不论是写什么的历史,其方法的后面都隐藏着这样的一个结论:社会是在向前发展,今天的现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就在这种单一的方法的指导下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是结论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创新可言,而且造成学科内部的资源浪费,学科重复建设也就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方法成了包治百病而又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走入死胡同的情势下,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1 (以下简称《中》)在大陆出版,自然受到普遍的关注。这一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而第二卷则于2001年完成出版。还是在第一版面世的时候,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但是葛先生无意于这些争论中的孰是孰非,而只是想在各种意见中得到一些更好的启发。葛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写到:
“我想,一部学术性的著作,作为一个文本产生以后,它就是公众评头论足的对象,作者没有权力对这些批评说三道四,特别是人文学科中的各种见仁见智,并不像是老吏断狱下判决书,更像是一种表达智慧和洞见的写作,而如今有引起书评的写作习惯,也不像是对被评的书发表针对性具体意见,而更像是借题发挥表示另一种高明的写法。所以,我想无论什么意见,赞扬的、批评的甚至是挖苦讽刺的,都无所谓,我也不愿意回应,只是内心里总是在希望,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益人神智的见解。”
如果葛先生只是想在国内的学者们的评论中寻找一种能够“益人神智的见解”,可能他会非常失望。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还没有人从葛先生所凭据的特殊角度来写作学术著作。更不用说是有着《中》这样扎实的历史学术著作。正如在文首所提到的,在总体历史观的影响下写出的史学著作,无不有着强烈历史失实感。但主要问题在于:进行历史叙述的主体的哲学基础的合理性能否与研究的历史事实形成配合。如福柯所说,历史只要发生了,用任何一种方法叙述出来都无法恢复历史的原貌。因为必须得有历史叙述主体的主观参与,历史叙述才能成为可能。所主观性介入的问题就成了追求真实的历史研究者无法解决的终极问题。但是,总体历史观所存在症结并不仅于此,而是在于以一种设定好的历史发展思路去指导研究。所以有这种知识背景的学者,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好的意见呢,最多就是以自己的总体历史观去攻击其他人的方法。
与总体历史观不同,葛先生使用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历程。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当中,福柯当算是这两种方法的开创者和实践者。而葛先生就是有意借鉴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关于考古学,《中国大百科书·考古学卷》就有这样的说明:
从现在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的历史知识,有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收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中的规律。
“福柯的考古学与后两种涵义有关。不同的是:福柯的考古学并不限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他将近现代的医学、人文科学等都作为考古学的对象;传统考古学寻求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福柯的考古学则注意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和不连续;传统考古学的对象往往是物质的遗物或遗迹,福柯考古学的对象则是知识。”2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了知识考古学方法,《中》就特别注重有关中国思想的文物的运用,特别是新近出土的历史文物。当然,历史学是注重考证的,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新方法以后,《中》中的历史性叙述就与之前的历史性叙述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点在下文还要论述。)
与此同时,总体历史观按照主观性的取舍塑造历史人物,与虚构性的写作相差无几。例如,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是不容置疑的圣贤。而在引入了知识考古学,考察了出土的文物和古代典籍的记载之后,葛先生写到:
“被称为文明开端的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说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贤,竟然如此的残忍和谲诡,……”(第一卷《引言》)
这样的结论对于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一直都在忽略这样的文字记载,而专门作思想研究的学者也绝口不提,他们从总体历史的原则出发,把自己的主观性带入到研究当中,因而,古代的圣贤只是一些被塑造产物,与真实也就相去甚远。而《中》的研究结论虽然对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冲击力,但是却起到一种祛魅的作用。
二
历史事实是一个隐没的在场者,即不能窥见它的全貌,也不能把握它的首尾。它也没有什么起源可言,因为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场域是一个在现实离场的事实,其中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吊诡的是,很多的事实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就生成了有机的联系,由此就有着叙述之魅。所以要使研究的历史事实有着合理性的基础,就不得不引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知识考古学所引出的历史叙述有着一种祛魅的作用。思想的历程通过表意符号传达出来,那么思想或思想的传达说到底也就是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所缔结的盟约。权力与思想有着依附的关系,同时也有着对立的关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者占有真理,与权力合盟。在总体历史观的指导下清理着思想史,得出的结论是思想史是没有断裂的、没有裂缝的。但是,在葛先生的《中》中,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这就导入了葛先生对福柯的谱系学思想的吸收。
福柯的谱系学源于尼采,但与尼采却不完全相同。在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思想。他指出,“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故而,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切的材料,要求耐心。……他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的展开,它反对起源研究。”3同时,福柯认为历史是断裂的,有裂缝的,而不是延续的。“总之,谱系学一旦除去真理、普遍、必然等的遮蔽,细节和偶然就会闪烁出熠熠光芒。尼采曾在道德的面纱下发现虚伪,在真理的宫殿里发出仇恨,在文明背后发现疯狂……沿着这条路,福柯将解剖刀指向更为隐蔽的领域:疯狂、监狱、性……福柯使我们讶异: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权力的网络中而浑然不觉,我们一直生活在蒙昧在而沾沾自喜。”4谱系学也是一种方法,而我们前面提到,葛先生的《中》是在吸收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而写成的。
正是如此,葛先生特别注意思想史中的权力的真理的相互关系。真理其实是一种话语,话语是一套带有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真理也就成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合谋。在葛先生的《中》里面,权力和真理话语的相互关系就成了思想脉络的主要依据。
在上古思想史,几乎没有异端的思想,真理也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上。他们是统治者,同时也是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真理就与权力形成了同盟。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真理与权力就时时处于分裂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而思想上多元化也就成了定局。“当那些无须论证就可以使人人平静地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力……”(《中》)但是各种思想却没有放弃对权力的争取。而当一种思想不断壮大,成为统治者认同的真理时,其它的思想或者隐没,或者消失。它们遭到了权力与真理合谋的思想的压制,但是有适当的机会就会发展起来。如葛先生论述到的佛教思想在清未的复兴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中国思想一直都是以儒家作为正统,处于权力的中心。似乎从汉代开始,自从汉武帝听从了懂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除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处于政治权力下真理的交叉点上,独占了政统的权力。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要开国之初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形象。合法性从哪里来,就从儒家的经典里面。如葛兆光先生论述到唐朝的时候,写到:
“唐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是有相当深的忧虑的,特中别是那个协助父亲从合法的隋朝那里夺取天下,又以并不合法的资格夺取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除了在政治上采用了相当开明和有效的方略之外,也曾经用开拓边疆平定四夷,羸得天下可汗称号的方式来建立威望,用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的方式来确认君主毋庸置疑的正当,同时,也是采用了相当聪明的文化策略,如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力,排定次序以提升政治权力在思想世界的权威等等。”
而在以后的几个朝代中也是如此,无论是汉人建立的国家或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都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解释,从而达到统治者占有真理的目的。
葛先生的《中》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思想史,因此,他的行文中一般会涉及到两个集团,一个是没有政治权力的士人集团,他们处于思想的边缘;另一面是拥有权力的统治集团,自然是处于思想的中心。士人集团想要争夺权力,只有通过思想的影响。而统治者为了保住权力权威,也只有通过对经典思想的解释。因而,社会思想就成了两个集团争夺据点。无论是唐朝的佛道向儒学的渗透,还是宋朝理学与皇帝为代表的新法的对峙,甚而是明朝心学与中央政权不谐调都体现了一个时代总体的思想状。(这一点,下文还要说到。)这些边缘的思想既然不是官方的统治思想,就带得有不合法的威险。但是都逐渐地得了整个社会的承认,形成了官方的思想,也就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边缘又在生成。
对于每一种思想的潮流,葛先生都梳理得很清楚,而且都是以谱系学的眼光来看待所存在思想的流变与消逝。比如说,写到清未的时候,葛先生写到了佛教在日本佛教的刺激下又复兴起来,这是很多的思想史里面没有提到的;还有在写到清考据学的兴起的原因时,葛先生认为有一个儒学重建的意味在里面。应该说上很具有说服力的。
总的说来,葛先生以系谱学的方法对现有的史料进行处理和梳理,在进行叙述的时候没有以往的历史研究者那样在思想思潮之间任意地建立联系,也任凭自己的喜好割断思想之间的真实关联。思想的流变在葛先生的处理当中形成一个个谱系,其中既有断裂,也有裂缝,而不整一的和没有任何变化的。
三
前面提到,葛先生的《中》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史,我想是基于两点。首先是一般的思想史对每一个思想流派进行考察和梳理的时候更能反应的思想状况;其次是非精英思想史的写作是考虑到思想接受中的普及性问题。一种思想并不一定就能引起普遍关注,也不是刚产生就能够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状,从而替代它之前的主流思想。葛先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不同,《中》并没有把任何一个思想家单独抽出来,进行介绍,也没有把任何一种在总体历史观的指导下认为不重要的思想潮流丢弃,故意忽略。比如,在《中》第二卷讲到几个后人认为了不起,又对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列出专章,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思想潮流里面,阐明他们的贡献。当然,讲到每一个思想家,也要考古他们的知识来源,清理他们的谱系。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才能说明一个思想潮流的流向。如讲到王阳明心学的时候,葛先生写到:
“其实那个时代,这种学风差异未必成为那么严厉的学派差异,思想兴趣的不同也还没有营造那么森严的门户辟垒,虽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信仰者常常要清理门户,维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从语词、学理、思路上说起来,朱陆之间,也就是理学与心学之间,本来并没有这么深的鸿沟,理学一脉本来也相当尊重内在的心灵对于真理的自觉认知,朱熹也讲“心即是理”,也承认“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只是他们比较看重对它的限制与规范,比较偏向于知识的积累和细节的体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被限制的实践主体果真慢慢地淹没在浩繁的经典注释中,然而到了明代以后,一批重视笃实践履的儒者渐渐开始突显“心”的意义……”
而王阳明只是把“心”的重要意义更为强烈地突现出来,引起知识世界的重大变化而己。而且王阳明的思想在他的生前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像王阳明在思考之后所服膺的陆九之渊之学,虽然在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尽管王阳明本身也已经以文才武功赢得相当的声誉,但是,这种异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在一开始的势头并不顺利。”这里葛先生强调了王阳明的心学所遇到的困难,而《中》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程朱的学说已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逐渐失无能为力束缚人心的力量。于是王守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宣扬儒家的道德规范是人人心中内在固有的先验意识,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代替程朱学说,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危机。”5
我们来看这段话中的不合情理之处,王阳明虽然是封建阶级内部的,并不能由此推出他的思想也就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而且还“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危机”。这些都不复合事实。因为当时王阳明在当时并没有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思想上更是如此,要不然,怎么在王阳明死后几十年才得到官方的承认?而相比之下,葛先生的叙述就要让人信服得多。他说:
“思想史常常把只是思想家的思想悬置起来,成为分析的文本,这当然是由于思想所发生的土壤和思想所进入的生活业已消失,但也常常是因为很多思想家并不注重思想的实现而只是注重思想的提出,这使得思想史无法确定这一思想对真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
所以,才有总体历史观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所得出的历史叙述和结论。
尽管占有的史料相同,但是方法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有些方法就是要求占有大量的史料,而有的只是在一些史料的基础上凭主观的选择,再加上演绎法而引导出结论。在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这部书,不但史料翔实,而且结论也让人信服。知识考古的方法与系谱学的方法相结合,超出了总体的历史观的局限。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扎实的著作,也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上海第一版。本文所引葛兆光先生的文字,出于该书就不另作注明。
24李晓林:《论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齐鲁学刊》,2001,(2).
3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46—147).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404—405).